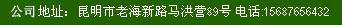|
作者为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爱思想网受权发布,转载需获授权。 日本,古亦以倭奴、东瀛、东洋为称,作为浩瀚太平洋上的“千岛之国”,厕身于无垠之天地,茫茫海天,反而有孤零冷寂之感。在外界看来,这个“千岛之国”常为雾霭所覆敝,也就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情,在孤冷之余,愈显得诡异和不可捉摸。日本是可爱的,雪山、海岸、溪流、温泉、瀑布,星罗棋布,造化神秀;日本是可怜的,火山、地震、雪崩、海啸、台风、战乱,也频频发生。一方面,时光静好,一方面,天地无情,这也就塑造了这个族群中“悲欣交集”的民族性。如同《菊与刀》中的深刻揭露: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这是一对矛盾的叠交。 有人说:“欧洲人是一种‘罪文化’,日本人是一种‘耻文化’,中国人是一种‘忍文化’。”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其实日本的民族性中糅合了“罪孽、廉耻、隐忍”三种性格,相对而言,日本人更喜隐忍,深谙“度心”之术。当然更深层次的,还有另外一种,是在这个民族的灵魂中挥之不去的,即“物哀”的性情。如同音乐《樱花》,弥漫着深沉的抑郁。 横滨港口 静美的横滨 5月19日,抵达日本海滨城市——横滨,今年是横滨开港周年,但她却散发出一种令人舒适的“古城之味”!横滨隶属于神奈川县(日本是“县”大于“市”,依然按中国隋唐的“县制”治之),作为日本关东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的人口规模是仅次于东京都和大阪府(日本的行政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的第三大城市。明治维新以来,这里一直是东西方交流与碰撞的前沿。 我对横滨的了知,最早源于对民国时期中国“东洋留学热”的学术兴趣。从近代史上,自横滨开埠以来,横滨与中国之间,便有着较深的渊源。由于孙中山先后七年以横滨为革命基地,横滨也被誉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仓皇之间,遁迹横滨,剪辫明志,并在此发明了著名的“中山装”。有趣的是,在横滨,孙中山与浅田春、大月熏先后邂逅;“情僧”苏曼殊负笈之际,也与横滨少女菊子相恋。看来,横滨是一座凄美而静好的爱情之城。后来,菊子蹈海而死,苏曼殊万念俱灰,归国于蒲涧寺出家,从此风雨飘泊,了此残生。苏曼殊尝言“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此番感慨,殊不知有“横滨之恋”中的几多哀怨?苏曼殊有诗云:“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这些都令人浮想到横滨对苏曼殊的另一番意味。傍晚时分,我与随行小蓝两人,漫步于横滨旧区,酒肆、寿司、烧卖、花店,各式小店,错落在幽深而静谧的小巷中,零零散散往来的人,充满日本风情的旗幡、昏黄光感的灯笼等,又兼晚来的风微凉,稍有秋的气息,给人时光流连之感。 近代横滨与中国的渊源太深了,以至于无法谈个究竟。次日,当我站在横滨港时,在港口前我来回蹀躞,思想起伏,我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当年的那些场景:年冬,鲁迅与陈子英在此迎接前来留学的范爱农及徐锡麟夫妇。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梅屋庄吉在这里接济风尘仆仆的孙中山、宋霭龄及胡汉民。年,辜鸿铭带着对日本亡妻的哀思,在这里乘船归国。横滨港,承载着当年这些人士的几多欢喜与几多哀愁?横滨港的海风吹拂,微凉,倚靠在海岸栏杆,一桩“公案”萦绕我心:年,日本医生山崎彪从福建漳州运走一尊中国和尚圆寂后的“肉身”,往事越千年,如今,唐代“无际大师”的“肉身”,依然“禅定”在横滨曹洞宗本山总持寺内。21世纪,横滨,在一衣带水之间,将依然是中日文化绕不过的话题。 东京的黄昏 东京落日 5月20日,进入东京。日本地形狭长,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其他多个小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约为37万平方公里,然而,可居住的面积却只有11万平方公里。一般人眼中的日本,土地贫瘠,资源紧缺,其实不然。日本素有“矿藏博物馆”之誉,土地也相对肥沃。只是,日本资源和土地的可利用率和开发率,相对较低。特殊的地理结构和地缘政治,构筑了异样的“岛国心态”和“岛国性格”。由于持续的经济低靡,首都东京,除了新宿歌舞伎町人头攒动,大部分地方显得疏冷。今天从日本“武士精神之父”楠正成雕像下走过,在天皇寓所前的二重桥留影,下午在自由女神像处流连。由于气候的原因,傍晚时分,东京港湾的凉风带有几分寒意,东京的黄昏,反有点“风悲日曛、愁云惨淡”的况味。突然间,令人想到这正是对这个号称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资本主义国家当下境况的写照!号称发达的东京,不过尔尔!人口老龄化,资本金融萧条,新生代的彷徨······这与绝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首都显然不同。 在自由女像面前,我想到了当前日本的矛盾遭遇:既强盛而又衰落的一面。恰如她的双重民族性格。当代日本有强大的一面:完善的社会体系、法制、教育、人文、工业、商业。整个社会,井井有条,高度自律,严谨有序,组织化程度高。在横滨的桜木町地铁口,络绎不绝的往来人群中,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熙熙攘攘,每个人脚步匆忙,高度自律。白岩松曾说,在东京地铁里,他震撼了,四周只听到噼里啪啦的皮鞋声,人人寡语而自律,这个民族有着高度的自觉和专注力。 日本“武士精神之父”楠正成雕像 前年,在暨南大学举办的“反法西斯国际学术论坛”上,我以社科联委员的名义,发表演讲,后来演讲的部分内容并被贾海涛教授推选刊登在《南方日报》“时事圆桌”版。当日的演讲我引述了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的说法,即今天世界上,在日本本土国家之外,还存在至少“个日本”。这“个日本”指的是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海外产业。“二战”以后,日本政府开始了长远的“海外殖民”计划,并力图构建“成熟的债权国”,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加速了重要资产的海外大规模战略转移,铸就了当前日本巨大的离岸经济。“个日本”是日本的雄厚“家底”,对其经济地位、经济状况的判断也决不能忽视。可以说,日本才是真正享受到全球化红利的国家,而且只有日本才是。如今,日本连续15年蝉联全球最大“债权国”地位,这是她与美、中诸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层博弈。 不得不说,日本的工业系统、科研体系是成熟而庞大的。超导技术、材料技术、纳米技术、硅技术、MEMS、以及在通信领域独占鳌头的NTT等,在诸多高新技术领域,也只有日本才能和美国“分一杯羹”。另一方面,我们熟知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丰田、东芝、索尼这些企业,他们不仅生产电梯、汽车、笔记本、手机、相机等日用产品,更有着另一重身份——军工企业,俨然构成了一个隐藏于民间的“军工帝国”。庄子说:“藏舟於壑,藏山於泽,藏天下于天下”,日本人可谓深谙此道。 当然,日本也有她走向衰落的一面,我总结为:一,当代丧失了优秀的如同铃木大拙、池田勇人等思想家、战略家。二,“物哀”笼罩下的民族性。三,新生代的精神沉沦(家国情怀的削弱、读书偏好的庸俗化、游戏动漫情色产业的大行其道)。四,国民缺乏国际视野(如:日本的民宅建筑都是封闭式的,整个民族对英文等国际语言的掌握程度差,社会趋向安逸生活的态度)。 静美:摄于伊豆长岗 侘寂?物哀?幽玄 5月21日,离开东京,赴伊豆。伊豆,出奇的宁静和祥和!最早对伊豆的闻知,源于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并至少五次被翻拍成电影。川端康成笔下的伊豆,既唯美。又充满“物哀”,《伊豆的舞女》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一种淡淡的忧伤,这与《菊与刀》里对日本人性格的剖析是一致的。我想起了在东京街头看到wabi-sabi店名时,不觉会心一笑。wabi-sabi译成中文,即“侘寂之美、残缺之美”,这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物哀”情怀,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和艺术,这种悲情植根于大和民族的灵魂深处,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主体,这又与悲剧神话塑造的古希腊民族性格有相似之处,决定了他们民族脆弱的一面。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核爆,90年代的“经济泡沫”,如今,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所宣之“日本经济崩溃论”,一直笼罩着日本社会。在21世纪,只要大和民族再受重创,“物哀”的性格很有可能导致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在这一点,我更倾向于《李光耀观天下》中对日本未来的悲观:在21世纪,日本将“走向平庸”。 “物哀”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理念,既是日本人的世界观、审美观,也是日本人的生死观。譬诸,新月、花蕾和落樱是日本人所挚爱,三者均精美而易逝,譬如樱花的花期一般为3到5日,之后就会凋零。这种“无常之悲”和“哀愁之美”的结合,正是“物哀”的精髓,并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他们籍求在“须臾之美”中,去体味“永恒之静”。如同三岛由纪夫所说:“美之所以美,乃是因为它灭亡。” 摄于高野山金刚寺 在我看来,“侘寂?物哀?幽玄”,这三个概念是理解日本文化的必由之门,也是日本精神的主轴,唯有如此,方能入其殿堂,窥其堂奥。“幽”者,深也、暗也、静也、隐蔽也、隐微也、不明也;“玄”者,空也、黑也、暗也、模糊不清也。“幽”与“玄”二字合一,是同义反复,更强化了该词的深邃难解、神秘莫测、暧昧模糊、不可言喻之意。这三种思想,其实与唐宋的中国士人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和脉承。一方面,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狂热,几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就拿最普遍的来说,宋代的“斗茶”风气、插花风气,都深刻的烙印在日本民族的身上,影响了他们的花道、茶道。日本的“侘寂之美”,悲剧、冷飕、凄寒美学,千利休的“清静和寂”,莫不源于宋之影响。另一方面,奇妙的是,中国精神传到日本,日本人没有全盘吸收,而独钟情于其中“侘寂?物哀?幽玄”的一面,想来怪诞。如中国古乐中宫(C)、商(D)、角(E)、变徵(F)、徵(G)、羽(A)、变宫(B)七种,变徵相当于现代西洋乐的F调,声调悲凉,中国古人多不用,然在传入日本以后,日本音乐中,却颇好变徵之音,悲凉而沉郁。 日本人喜欢曜变天目茶碗,并将一只宋代的曜变天目茶碗,奉为“国宝”。日本人喜好抹茶,但茶汤入曜变天目茶碗后,俯视之际,彷佛有星空绚丽璀璨、曼妙缥缈之神奇。日本人对曜变天目茶碗的青睐,正是对“侘寂?物哀?幽玄”的精神哲学的融入。到了茶祖千利休之际,“清、净、和、寂”的美学成为主体,一只完整的碗,已经不符合孤标卓绝的审美意识了,于是有千利休“手斫残瓯”之典。这种“孤寂美”、“残缺美”,其实与宋人“马一角,夏半边”、“剩山残水”之审美,是相接壤的,是一脉相承的。乃至于在当代,在我看过的一些日本电影中,诸如《燕尾蝶》、《情书》、《寻访千利休》、《入殓师》等,这些优秀的文艺片,其主调也都弥漫着一股哀思。 从东京到伊豆,在我走访过的大大小小的各式“神社”中,无论从建筑、格调、感观和精神上,也都无意间渲染着“侘寂?物哀?幽玄”的情绪。日本信奉的是“神道教”,不是佛教,“神道教”是国教,所以,在日本,“神社”遍地可见。“神社”并没有具体供奉的神,反而空空荡荡,中悬一钟一绳,显得孤兀,表达了大和民族特殊的信仰体系,即“敬天敬地敬自己”,这与佛教禅宗中的“自性说”“般若说”非常相似。所以,日本民族的高度自律,从深层次讲,也是神道思想的一种意志力体现。 地主神社:摄于东京 大阪城下 5月22日,游京都,23日,到了大阪城下。这是丰臣秀吉苦心孤诣经营之处,在这座城中,他挥斥方遒,开疆拓土。大阪城下,我浮想到了年前,丰臣秀吉在此提出“中国诚为日本之大患”的言论,开始了年侵华之布局时的场景。可以说,丰臣秀吉是“中国威胁论”的揭橥者。 年,美国上将佩里率领的美国海军舰队来到日本,史称“黑船来航”,日本被迫开放,于是开启了“明治维新”。年,明治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直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彼时开始,一切的学术也都开始围绕于此,时至今日。于是,日本人出现提倡“和魂洋才”的佐久间象山,“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伊藤博文。 丰臣秀吉营造的大阪城 日本曾经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中国通”,比如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伊藤虎丸、丸山升、太田辰夫、吉川幸次郎、松浦友久、内藤湖南等。然而,在我对他们的著作进行解读之后,我却惊讶的发现,日本“中国通”的学术,基本可归为两类,即“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而后者,从他们对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社会结构、族群宗法等的研究,几乎严谨到了苛刻的地步,我几乎得可怕出结论:一旦前者成功征服了中国,后者会比中国人更清楚如何统治中国!持此惊世骇俗之论者,自唐某人始。 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的研究是苛刻的,乃至于是刁钻的。如从年至年,日本在华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通过培养了大量的所谓“中国通”,以“大旅行”、“大调研”手段,对中国进行地毯式的研究,形成了上亿字的报告。又如近年来活跃的学者野岛刚,他在《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一书中,通过对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刁钻式研究,最终从字画中窥探了大宋不为人知的一面,即深藏在繁华背后的社会危机。以此重新解读北宋社会史。 在学术上,近代中国反而受日本人影响至深。“封建、哲学、国体、主义、意志”等多个词汇,都是从日本回传的。举隅“封建”一词,马克思将欧洲中世纪“庄园经济”下的“领主制度”,称之为“feudal”,日本人译之为“封建”,国人不加辨析,深套国史,把中国秦以前社会称为“奴隶社会”,把秦以后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实则谬以千里。秦以前社会,才是“封建社会”,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之“郡国制”。秦以后社会,“废封建,置郡县”,以至明清之末,实属“专制社会”,如何能以“封建”论之。此事虽然我曾多次公开阐述己见,但也确实印证了近代日本对中国影响之深。 下榻在大阪的酒店海阳阁 抛开民族情结,在我看来,近百年日本,几次以“国运相赌”,有成有败,也反映了大和民族对其未来命运的历史思路。第一次“国运相赌”是成功的,即:一,脱亚入欧。始作俑者,明治维新以来福泽渝吉,伊藤博文诸人。第二次是成功的开头,失败的结尾,即“二战”军国主义的军事殖民路线。其谋略者,以昭和时期侵华的“三大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及“军谋巨头”石原莞尔等为代表。第三次是目前正在实施的“全球工商业殖民”。借助全球化、工业化、及资本主义契约精神,建立海外重工业,商业等,用资本左右世界。第四次以“国运相赌”是现在和未来的“终极大计”,即“百年海外移民计划”,二战以来,日本一直有计划有组织的派遣优秀人员海外移民,学习犹太民族,并建立庞大的工商业系统。 这里有一个历史细节,年,年轻的日军战略家石原莞尔,在武汉汉阳码头,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留下了“(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等论后,慨然远赴德国。本来,他为日本设计的第一个方略,是联合中国,代表东方去博弈西方,然而中国之行,却让他成为“脱亚入欧论”的最后压轴者。至于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在其死后,史学界还长期流传着他能讲十三种欧洲语言和四种汉语方言的故事。还有鼓吹“亚细亚主义”的权威人物——大川周明,他是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民间人士”,在他的理论核心中,日本应当担负起“拯救亚细亚的重任”,为此必须建立独裁政权,是大东亚战争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操刀手。大川周明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精通中文、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早年深入钻研于吠陀文学和古印度哲学的学术大家,如何成为一位法西斯主义者。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性格诡异和突变的一面。 在大阪的心斋桥,如今繁花似锦,人头攒动。我努力想象当年辜鸿铭到此吊唁和哀思其日本爱妻的情景,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在心斋桥的熙攘之中,我走进一间冷清的书店,购买了一本年明治维新时期的木刻版线装书《大日本史》(残本),心中颇喜。对于这个民族而言,如今有不幸的一面:文化断层。曾经日本有很多优秀的“中国通”,内藤湖南、沟口雄三、伊藤虎丸、丸山升、吉川幸次郎等,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但是,一个号称热爱读书的民族,此次日本之行,在我走过的林林总总的书店中,“中国通”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却多被当成白菜价贱卖。相反,充斥各大书店热销的,却只有两类,漫画+情色书刊。真替日本民族的下一代忧虑!彼时彼刻我在思考,唯有李光耀对于日本之观察是至为老辣的。 我想起了在横滨时,无意间走过一些游戏机室的片段。令人惊讶的是,游戏机室内满是老年人的身影,这让我颇为惊讶,这些老年人没有沉淀下来,却把暮年消耗在无谓的游戏机室中。在横滨走过的所有书店里,每间书店几乎一半都是漫画!漫画,游戏机,色情店,遍地皆是。令人不得不感慨,“二战”以来,这个民族的民族性中,“菊与刀”中“刃”的一面,早被美国潜移默化的改造和摧毁了。在一间古旧的川崎书店,日本先贤们满是研究中国学的著作,如今被鄙夷摈弃,0日元原价被日元(折合人民币6.5元)贱卖。年轻人不大那家医院治疗白癜风好白癜风医院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醉美色烟台之秋,唯有爱与美景不可辜负
- 下一篇文章: 黄山各地积极开展全域环境整治